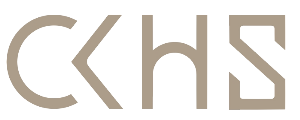早已習慣的清晨五點五十的日出,緋紅的陽光照映在社區裡的藤槭與杜松林裡。葉子好像火燒一般,這大概是每日鬧鐘響之前,窗外最美的十分鐘。瓦斯爐上的摩卡壺不一會已嘶嘶作響,今天應該不會太忙,幾個門診而已,但每次這樣想幾乎都會晚下班。
來北美訓練,轉眼間已要邁入了第四年。獸醫外科是個冷門且孤獨的職業,一年大概有五十人完成訓練。從頭頸手術、開胸開腹,到泌尿、骨折修復、關節置換,成功的關鍵在於對解剖與生理病理的掌握。投入的時間成本之多,若是不夠癡狂、不夠熱情,真的不是正常人會想做的事。想著想著,似乎覺得怎麼又是在挑難走的路走?這感覺卻很熟悉,似曾相識。高中畢業已十一年,再沒幾個月就要三十了。自始至終,我認為高中在建中樂旗隊的經歷影響最深。
還清楚記得,那是在國中畢業、基測剛放榜的暑假,沒見過幾次面但是是國中管樂隊死對頭的韓念祖,用即時通敲我
「你要加管樂隊嗎?他們好像是樂旗隊,要走室外」
「?那是什麼?」
「youtube…………」
我也還清楚記得,幼稚園大班就認識的黃子軒,也考上建中。在我們決定要參加樂旗隊後,也聽說他要加入的消息——我們要繼續同班三年。也還記得招生說明會、記得第一次中午組練,在自我介紹完之後,幾乎沒被罰過站的我(們)就被鍾仁文訓練立正,整整站了幾十分鐘。
我們這屆是第一屆、也似乎是唯一一屆高一就分在同一班裡。早上一起晨練、白天一起上課、中午一起吃飯、晚上一起團練,真的是除了睡覺之外幾乎都混在一起。建中樂旗26屆對高二學長來說,應該算是乖巧安靜的一屆吧,自己說。
若一一細數,有太多的細節隨時都能從儲思盆裡被抓回來。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在意建中樂旗隊。樂旗隊的訓練、表演,一樣是冷門且孤獨的。每一步的大小、角度;每一拍要對的人跟點;每一樂句要放進去的想法,沒有千錘百鍊是刁不出來的。一整場十二分鐘,從設計、練習、修正,到最後的表演,沒有半年十二個月,根本不可能。這群人,專挑難走的路走,投入的時間成本之多,若是不夠癡狂、不夠熱情,真的不是正常人會想做的事。

今年夏天美國東岸,是「第十群」 十七年蟬的季節。上一次第十群出現,是在2004年。那時我還在念國中,社群軟體剛剛出現,雅典奧運臺灣首面金牌。十七年蟬,半翅目,蟬科,周期蟬屬。擁有深黑身軀、血紅眼睛、橘紅翅膀。他們身長約2-3公分,同時也是世界上壽命最長的昆蟲。他們將席捲美國東部、中部、以及南部,在4-6週內求偶、交配。接著,像是種下什麼一樣、像是把記憶深埋土壤。他們產卵,讓這一切十七年之後再來一次;然後,當時候到了,他們在蟬鳴高潮中驟然死去。他們會覺得可惜嗎?等待了十七年,好不容易羽化找到同類,卻很快地結束。有些事情大概就是這樣,蟄伏期待就是為了那短暫絢麗的精彩;有些事情大概就是這樣,曾經擁有過,也就夠了?
不,不夠,也還好不夠。為了要繼續找到這稍縱即逝的成就感,高三、大二,校友回隊參加表演,永遠都還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大三暑假跟庭瑋來美國參加行進樂聯盟比賽、之後參與教練團,我們常常笑說我們大概是中毒了、成癮了。
2019年夏天在加拿大做小動物急診訓練的那一年,建中樂旗隊正好到距離我六百公里的卡加利比賽。那天早上我從大夜班下班,九點半快樂地回家洗澡,中午去機場,三點多抵達;從德州飛來的鄭期文接機,把我載到決賽場地。這趟快閃行程,我見了想見到的人們、用力刷了一下存在感,15小時後就趕上回去的航班。其實最讓我深刻感受的,不是史上海外最高分的表演。而是在場上看著隊友們全神貫注踩著每一步,一起逐漸完成任務。十年之後的這天,對比十年前在場上迴響的 Quidam,完全讓我重溫這樣深刻的感動。一切都是那麼熟悉、一切都是那麼觸手可及、一切又是那麼遙遠。
在美國獸醫教學醫院,每四週都會有新的實習醫師來輪外科。我們總會在一開始時先自我介紹一輪,然後總會提一下,如果不是獸醫,我們會選什麼樣的職業。行進樂隊教練吧!聽起來實在是八竿子打不著,學生們大概也滿頭問號。不過對我來說,行進樂隊訓練、與獸醫外科專科訓練,很像啊!
*這篇文章寫到後來,心裡對范家銘與賴孟泉兩位教練、26屆與上下幾屆夥伴的感恩、以及對過去一起相處時光的懷念難以平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