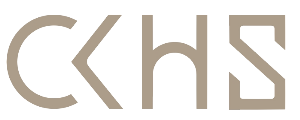本文刊登於2024校友俱樂部報紙專訪
Q1.先聊聊教官您的成長背景?是什麼樣的機緣投入教官一職?
我不是大家認為的軍校生,是預備軍官。當時是考四年制的志願役軍官,不是兩年的義務役。為何會去綁約四年預官?大概是當時環境有種氛圍,自己不是那種會唸書的人,那時也缺預官,四年可以交給國家栽培,若能考進去好像是個不錯的選擇。加上聽聞預官之後可以報考與從事有雙薪俸的教官職,太吸引人了,這完全是我想要的路。但後來發現,關於雙薪俸這件事,我被騙了!
回憶當年考教官的過程,也聽聞是按照成績分發學校的,所以大家都很努力!我分發的那年,金門缺額兩位需要靠抽籤決定,我就是那其中一位幸運兒,當我被抽中的當下,全場歡聲雷動,正是感謝我幫大家頂住籤王。但意外的是,當分發通知單寄來時,上頭分派地點竟不是金門,是台北市。聽說當時是因為有人自願申請到金門,原訂抽中的名額就被取消改派台北市。不然,當時我一切都準備好要去金門了,因為只要在金門服務過兩年,以後的單位都能自選。當時真的覺得好遺憾沒守住金門這個機會!
不過,老天幫我關閉一扇窗時,也為我開啟另一扇窗。到了台北市政府報到時方才知道我的分發單位,建國中學就是我教官職的第一所學校。
Q2.多數人對於教官這角色感覺是嚴肅不好親近,但是這個角色似乎也建立了學生在課業之外一個心靈的出口,扮演老師或家長們無法取代的角色,甚至是一種如兄如父的榜樣。
這角色的魅力很特別,這是老師和家長之外,有哪個部分是教官可以補足的?您覺得為什麼會有這樣角色的存在?
來建中任教時,首先負責高二生,而我只大當時的建中學生七歲,真的就像兄弟般的感覺。但做為教官的工作,仍不能失去身為師長的角色。在兄弟和師長之間需要拿捏取其平衡,尤其建中的學生很優秀,我經常要動腦和他們磨合。
當時的建中除了白天的學生外,還有建中夜間部和建中補校。想當然耳,建夜和建補的學生和日校的學生是有一段的差距的,但我們看到有行為偏差的學生一樣要糾正,但往往在嚴厲糾正過後,隔天我們教官們的汽車鑰匙孔就會塞滿樹枝和快乾膠,學生就是要跟教官槓!這些經驗也讓我慢慢學著如何與兩種不同風格的學生溝通。
當年建中還有住宿生與外宿生,我們也要管理與關心。「住宿生」的宿舍是原建中的資源大樓的位置,大部分是建中補校的學生,還有當時的僑生。而「外宿生」則是許多中南部的學生考上建中,住宿在學校附近的租屋處,這些學生都需要留資料隨時關心。
當然,教官也需要關注學生的心理層面,經驗多了也會慢慢知道學生在想什麼。我們會和輔導老師討論如何協助學生約談與關懷,外宿生會有家訪等各面向的輔導機制。也會常常在上課時從教室後門偷看學生,若發現學生行為不恰當時,會私下關心,不太會有什麼正面衝突。
建中九年執教期間,我和樂旗隊互動的時間算是最多的。從第九屆建中旗隊開始,尤其當時的訓育組長溫貴琳組長和我一起共同創立了「樂旗隊」,確實見證了當年從樂儀隊轉變到樂旗隊的過程。
第十屆之前建中只有樂隊和儀隊,沒有旗隊。當時台北市公立高中只有中山女高有旗隊,讓我們開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做點改變。當時創業維艱,我和溫組長就絞盡腦汁思考如何可以生出旗竿,就去地下室找到一堆國慶用的國旗竿,將全部鋸成180公分,用當時現有的救國團團旗來練習。雖然道具質量都還未達正式操作的標準,但先求有道具練基本功,就是當時首屆樂旗隊誕生的樣貌。
後來,學生也跟進學著募款,有資金之後,就去買了碳纖維的旗竿,當時從中山女高來的劉昭玟教練也給予很大的助力。不過首屆旗隊成立時,不少同學是充滿抗拒的,尤其要被編入擔任旗隊工作的同學會覺得那是女生在做的事,被叫去學拿旗子感覺很不是滋味。後來劉昭玟教練認為旗隊也有陽剛的一面,這正是一個創新的機會。台北市每兩年都有一個樂儀旗隊的交流賽,我們第一次成軍之後就在首次參賽中打敗中山女高,是一個令人鼓舞的時刻。
這是建中樂儀隊轉型為樂旗隊一個歷史性的一刻,溫組長和我當時正是這個轉變的重要推手。至於我為何與建中樂旗隊的感情那麼好,是因為當時經常需每週陪著這這群樂旗隊的學生到中正紀念堂訓練,和樂旗隊在一起的時光確實比一般建中的學生還要多上4-6小時。當中還真的建立了不少兄弟情誼!
教官這角色在學校是扮演學生行為上的輔導者,經常也是老師、家長另一個溝通的橋樑。就像建中樂旗隊當年轉型的過程,為了讓家長認同樂旗隊存在的價值,第九屆開始成立了專一的樂隊班,將之界定為資優班。給予最好的教育資源,學生有了好成績也能給家長一個安心的交代。甚至有學生家長常來教官室質問,他們認為孩子來建中是要唸書的不是來表演的。我們要如何改變家長、師長的刻板印象,花不少時間給家長曉以大義,慢慢了解孩子代表學校出賽是一份無比的榮耀。教官們也經常在這些大小的歷程中和學生一同成長。
特別一提,和一般班級不同的,樂旗隊是一個很特別的團隊。大家重視團隊合作,透過無數次的團練、比賽、出任務,已磨掉彼此的心性,少有敵我意識,願意正向看待問題,促使課業上更懂得相互照顧。與其說能K能玩,更不如說是這個團隊成就了後面更多的事情,樹立了樂旗隊獨有的團隊榜樣。
Q3.在建中九年的執教生涯裡,有沒有學生比較調皮的行為讓您印象深刻?例如建中生爬牆時,您都如何處理?
爬牆當然有,那個牆兩米多,不讓學生爬,主要也是怕學生跳下來會受傷。記得第42屆的三十重聚我受邀參加,一位學生突然跑來跟我說:「教官,我是來報恩的」我問:「為什麼?」他說:「謝謝教官當年在我爬牆的時候沒有記我過,只要求我不要再爬牆和這樣跳,是擔心我受傷。」「若您當時記我大過,我則無法考醫生。」現在,這學生在大醫院工作,還說教官以後看醫生就由他來照顧。還好當年我愛的教育,才有這位醫生的誕生與後續美好的連結。
另外一個學生的故事也很有趣。當時高中教育規定,曠課超過20節課是需要被退學的。我記得一位第45屆的學生當時經常溜去校外看漫畫,他已經曠課19節課了,我還是先找他的家長來懇談,後來雖然已經達需被退學的門檻,但我看這位學生後來願意收心回學校上課讀書,就放他一馬,之後也安然的畢業成為一位醫生。多年後我遇到這位差點被我退學的學生跟我說:「教官,我的診很難掛,您來我們直接安排VIP。」
過去還有一位心情低落帶酒到學校的學生,我當時只請家長來學校了解狀況,沒給學生記過,後來這位學生的家長還意外成為我的鄰居,相認之後這位爸爸特別感謝,我當年沒記兒子大過。後來雖然這位帶酒的學生大學聯考沒有很如意,但沒有因此放棄自我,後來在大陸生意也做得有聲有色,得獎無數,也創造出一段精彩的人生。
現在回想起這些點滴滿是懷念的,儘管當時有一個比較嚴重的行為,在人行道騎機車撞到人這事件確實不得不嚴格處理,以及當時幾位建中學生在校外抽菸被我記警告外,印象中我還真沒給學生記過的經驗。不能因為學生一次的犯錯或好奇就當下否定學生,畢竟都是尚在學習的高中生,不完美是養分,我們僅是他們學習路上的陪伴者,如果說教官存在的意義是什麼,是如兄如父的榜樣吧!
Q4.從威權時代到今天,教官這角色也因為時空背景的轉變有了不同的定位。
您如何調整心態看待這些時代變動的轉變?
在軍中部隊中,對下就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但學生不是阿兵哥,不能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當時在師範大學接受擔任軍訓教官的職前教育也會特別要求,我們面對的是15-18歲的學生,和18歲以上阿兵哥的方式完全不同。
當時有個校外組織叫「中學生XX聯盟」已忘記全名,在這聯盟裡有許多是來自台大歷史系、政治系等的學生,甚至當時許多建中學生的家長也是這些大學的教授,學生多少會感受到社會氛圍已經不一樣。加上解嚴之後,自由空氣瀰漫,這個中學生聯盟的成長飛快,成為一個很有影響力的校外團體。這團體的人經常在凌晨4、5點時到建中的各班教室丟宣傳單,宣傳單上大多寫著「學校教育哪方面的不合理等文字」,學生看到就會感到非常新鮮。
當時,教官們當然會擔心這樣的思想或情緒會被散播,於是也進行許多對策因應。剛萌芽時期,我們還能直接跟建中學生收回傳單,後來只能用更積極的方式應對,我們就在5點到校巡教室,那時站在操場時都會看到他們成群結隊到教室丟傳單,我們只是提早到校嚇阻對方,並沒有抓人,等他們發完再去收傳單。嚇阻過後有點效果,他們很久才再出現。
雖仍屬萌芽時期,但在那段期間也是有建中學生真的做了一些史無前例的行為。記得某年校慶,司令台前有個講台,老師們要開始整隊的時候,講台邊突然鞭炮響了,學生一陣歡呼,當時的主任教官非常火大,經過調查也找到當時學生惡搞的原因,就是想讓一個正規的典禮來點新火花。
另一個事件,就是那大約是國民大會的最後一年,當時不少傳單盛傳老國代要退出國會的議題。於是,某回升旗時,司令台背後建築物四樓高的地方有幾位學生做了一個大布條向下垂放,上頭寫著「老國代退出國會」等字眼,當時學生放下紅色大布條後立馬跑走,我們沒追慢慢走,就是要看學生可以跑多遠,後來在教室發現一位氣喘吁吁的學生,就知道那是現行犯。但我們也沒有嚴懲,只告知別再幹了!
當時會在地上噴字的一群人,流行叫他們是一群「小蜜蜂」。當初自己在看這些和過去保守思維對抗的行為其實是很不習慣的。那也正是現在民進黨的萌芽時期,這就是一個社會的發展,我也不得不試著去理解它。若我一直故步自封,不跟著社會的變動調整想法,其實我會過得很痛苦。所以,我常告訴自己,任何時機都是在做學習,自己要調整步調,持續關注社會,不讓自己與環境脫節,才能與時代共存。
現在,我經常和朋友分享:不只是「過好『生活』」,而是要「過『好生活』」。離開在建中服務九年的時光之後,我也到私立高職執教九年。退休之後,生活沒閒著,持續工作到疫情前。現在一樣充實忙碌,攝影、烘焙都認真的玩,實現「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