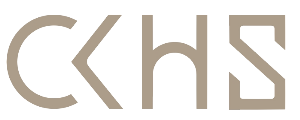本文刊登於2024校友俱樂部報紙專訪
Q1.您何時發現自己對音樂、歌唱充滿熱情?是否有什麼樣的契機與信念引爆您勇敢爭取自己的熱情?或是同時有什麼力量在阻止您?
在台北醫學院求學期間參與學校合唱團開始,應該就是把我從醫學院串接踏入表演藝術圈的關鍵時期吧!北醫合唱團期間,透過他人的回饋,深知自己能唱還能演。加上台灣當時的傳媒時空就像一塊海綿般,不斷地引進與吸收,音樂媒體相當蓬勃,歐美音樂文化是正值少年的我所嚮往的,例如音樂劇的表演樣貌讓我深深著迷,這些能量促成我邁向演與唱的道路。接著很多團體陸續邀我表演接案,我義無反顧的投入及朋友們一連串的協助,就這樣一步步形塑現在的我。
有沒有阻力,當然有。在表演圈子的不確定性經常是接踵而來的,加上我是一個對事情很執著的人,儘管對未知充滿壓力,但我還是想要為自己想做的事努力辦到。過去我甚至會把父親的不認可當作我逐夢的動力,我不會因為父親的不認可而去恨他,反而會想我該如何達到他期待的樣子,或是思索我哪裡還做得不夠好?自己內心會一直在尋找這個答案,心想總有哪天我的父親可以看到超出預期的我,應該是那種化阻力為助力的歷程。
就在疫情期間,父親是在事隔二十多年後首度正式走入劇場,看了我主演的「四月望雨」那場戲,對我來說當然是很特別的一夜,就像一個大扣子打開了的感覺。但當天我沒有痛哭流涕,因為這麼多年,我也能理解父母多年的不信任,他們多年的關心是非常辛苦的,「時間」最後也成了我們親子間和解的一把鑰匙吧!
Q2.您有能唱能演的天賦與特質,是否和您自小學音樂有關係?特別過去您在媒體提到小時候是自己主動提出要學鋼琴,這個認識自己的契機是?
我很享受做一件事是可以讓大家因此感到驚艷、或是被感動到,像是一種瞬間會被我的表演抓住的那種感覺。這時我會因那種互動中感受到自己存在的意義。就像我指揮、我彈琴、我唱歌,那種可以抓住他人眼光的瞬間,很美妙!演奏樂器就是可以很快讓身邊的人有這種感受的,啟蒙我的鋼琴,算是我表演藝術之路最初的老師。
在建中加入樂旗隊後會選擇打鼓也是蠻妙的安排,高一時看到負責打鼓的學長在朝會時以極速的打擊節奏迎面而來,那個畫面非常震撼,就是帥,當下就決定我也要像他一樣帥,成了我與打擊的串接。到底多愛打鼓,除了練習、幫大家寫鼓譜外,大學聯考前我放鬆的調劑方式就是去教學弟們打鼓。我很執著,當選擇要做這件事時,總是義無反顧的想做好。大概就是這個性,慢慢受到肯定,高中時期音樂的投入也成為探索熱情的起跑線。
當年大賽時與時任校長劉玉春校長合唱
巧遇當時的少女偶像明星何雨雯並合照
Q3.成為醫師前,您是否曾有念頭想在醫學和藝術之間做個抉擇?考上醫師執照後,對之後的音樂發展有任何好的影響或是不好的影響?
當年的氛圍,能考上醫學院是一件相當備受肯定的事,我到沒有想過選擇不去唸的想法。儘管藝術魂在內心持續燃燒,我覺得仍須以考取醫師執照為優先。至少保障自己,就算藝術夢沒達成,我還是可以回來當醫師。
以前會覺得有醫生背景這件事對表演藝術是個枷鎖,因為還是有很多人會覺得好好醫生不當,來戲劇圈卡位很不得人疼,經常是自己給自己設限。但漸漸發現我特別的身份、能力,不是枷鎖是祝福。
現在回想一路走來做的每件事好像都有反作用力出現。就是我在紐約求學時會經常去看百老匯的音樂劇,這些經歷影響我很多。特別是音樂劇「42街」(42ed Street),因為當時可以用便宜的學生票進場,我至少看了十幾次。由於都坐在最前排,能夠近距離感受到舞者的張力,每次看內心都是激動的,到現在仍覺得那個感動是相當滿足的。另一齣音樂劇「夢幻騎士」(Man of la Mancha)其中一首「The Impossible Dream」每次聽都備受感動,其中塞萬提斯在獄中要大家試著「相信」,當我們願意相信那個事情是真的,就會變成真的。這樣一個對「相信」的推波,在很多戲中都能強烈感受到,一直到後來我自己站在舞台上演出時,那種感覺就是「相信」帶來的力量。
劇場是有魔幻力量的,它常會幫助我們解開一些結界,經常在生命當中的各種時刻把很多事情串連,一起共感共情共鳴。後來也發現醫學生物和音樂藝術是有許多關聯性的,因為我會好奇是什麼樣的染色體組成或是什麼樣的生命故事會淬煉出人的各種情感樣貌,醫學或生物學確實會幫助到我看待這些魔幻。
Q4.您對於想做的事情會義無反顧,如果很投入劇中的角色時,是否會抽離不出來?您如何克服這種挑戰?
我去年接演的百老匯作品「近乎正常」(Next to Normal),這是一部榮獲普立茲獎的音樂劇,預計在2025年下半年會在台北加演。這齣劇和過往音樂劇最大的不同是其演唱的譜非常瘋狂,全都是高難度的爵士譜。其戲的台詞也很狂,把台詞說完後,自己就很容易陷入那個情緒漩渦中。我飾演這劇中的父親,演到最後大家都選擇離開這位父親,當時我的情緒真的降到谷底,很需要被安慰與擁抱,難度很高,表演過程中我一定毫不保留自己的戲魂,全心投入演出,確實容易卡在情緒中久久無法自己。
至於怎麼抽離,每個演員的方式不同,這齣戲當中後來我決定安排用一句唱段讓自己也讓觀眾知道我這個角色沒有陷入情緒泥沼裡,最後我是站起來了!這樣一個安排也是幫助了自己回到現實面。
談到克服挑戰,我想,像我這樣一個由醫師成功轉換到表演藝術工作的歷程,就是一個很大的克服,在台灣表演藝術圈裡算是先驅吧!若我這樣的決心都能創造可能性,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但我特別想說的,Next to Normal的角色原型在揣摩這個角色時,其實參考了很多我父親的形象,他對家的支撐與溫柔的堅持。所以,回顧這些年,我克服挑戰的主要力量就是來自於我父親,來自於他多年的容忍,還有家人的信任,若沒有他們堅定地守護,我現在不一定有機會成為演員,也無法有機會透過我的聲音傳遞生命的力量,謝謝我的家人。
Q5.在多數台灣人眼裡,做舞台劇不容易生存。台灣的舞台劇一路走來也都相當挑戰。就您的觀察,可以如何改善這樣的生態與跳脫這種刻板印象?
台灣劇場表演和二十多年前大學時期的生態已經很不一樣,像老朋友也是校友的陳午明一起在神秘失控人聲樂團締造很多佳績,各代的團員也做發揮了很多影響力,大家這麼努力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把大家從家裡拉進劇場裡,讓大家能在一個空間裡專心一個半小時好好看劇,讓舞台劇裡的故事能觸動大家的內心,這就是舞台劇存在的價值。
現在回顧我二十多年前的決定與方向是對的,因為台灣如果要越來越文明,戲劇音樂的傳承是不能貧脊匱乏的,這是一個成熟社會不可或缺的發展。